另一个世界
不喜欢诗歌的人,也不会喜欢摄影,明白吗?
——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选自《美国人》序言
终于,这期工作坊再也没有一个“摄影记者”报名!
终于,这期工作坊再也没有一个人用照片叙事!
终于,当年设立这个工作坊的初衷,在新的摄影业态下迅速旁落!
但这个工作坊却意义重大!
2012年,以新闻摄影前辈徐肖冰先生的名义设立的这个“青年摄影师工作坊”,起初的动机相当单纯,就是帮助入行不久的青年摄影记者解决“技术”瓶颈,成为一个更好的摄影记者。也就是说,要让摄影记者成为更好的“专业”工作者,要让报道摄影成为更“专业”的摄影。
现实变化太快了!仅仅十几年工夫,摄影的生态天翻地覆,“专业”迅速被“非专业”取代:由社会公器变成个人表达;由向外的反映事件转为内在体验的外化;由及物变为不及物;由强调共同经验范围转为不自证、不反驳、不妥协……
在工作坊结束的总结会上,我用“溜索”和“漂流瓶”比喻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前者尽管也有风险,但由此及彼,目标明确,你我等距;后者则无具体目标,无时空限定,几乎不可预测,充满了随机性、不确定性以及宿命般的漂泊。
这还只是外表的区别。更本质性的改变是:
1. 碎片化以及碎片化的组织成为重要的语言方式和表达方式。这些经过仔细截取和谨慎重组的碎片把“事”排除在外,消解了以往报道摄影以建构“二元关系”为中心的“情节”;重新拼合起来的世界已经超越了原本的存在,它是多元的、立体的和动态的;它追求的象征也不是原本确切的、意义性的象征,而是弥漫的、模糊性的隐喻。
2. 意趣(feeling)取代了意图(intention),“发布”也就代替了“传播”。
3. 如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作家、文学评论家)所言,许多摄影者仿佛隐身于“中性”的观看:“中性,表现为一种‘准不在场’(quasi-absence)、无效果之效果的立场。”“几乎不在场”并不等同于新闻摄影所谓的“客观”,而是对眼前的一切不率先赋予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
4. “应和”,成为作者与被摄对象之间最重要的权力关系,它取代了原来的“代言”。所以,它不再重视报道摄影所强调的“特殊性”和“事件性”,而是看一个事物或事件能否成为“应和”的“客观对应物”,以便在特殊性的顶端起跳,在其之上绽放出普泛的一般性。用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哲学家、思想家)的话说,就是“作品绝不是对那些时时现存手边的个别存在者的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物的普遍本质的再现”。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在桐乡拍摄的照片,却并不具备多少“桐乡特色”的原因。
尽管如此二元对立的比较僵硬且危险,但它有助于我们看清变化的面貌并加以描述。更进一步的比较是,摄影的“可能性”远胜“可行性”——我更欣赏它多元而烂漫的生机和生动,也更希望它与那些终究当不上摄影记者的人的生命相伴,而不仅仅成为一种生存的手段。
这一期工作坊的学员大多是在校学生,或者刚刚毕业,大家不约而同地抛弃了摄影并不擅长的叙事,进入到象征(或隐喻)的领域,即诗的领地。在诗的世界里,我们所有的范畴——本质与建构、物体与影像、虚幻与实在、他者与自我、可见与隐晦,统统混淆在了一起。于是,经由摄影,大家兴许会让自己一度失散的灵魂重返自我,会让有趣的灵魂分拨儿遇见,一块成长,互相对视——摄影真就有“把事物变成景象,把景象变成事物,把自我变成他人,把他人变成自我”(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哲学家、思想家]语)的神奇魔力——它让我们互为镜子,比如:
段浩明和贾江凡向我们展示了初始图式(initial schema)作为基础性的图像概念,如何在需要短时间内完成拍摄任务的预备中起效。段浩明的《运河两岸》秉承了自杜塞尔多夫学派以降的景观图式,冷静、中性、收敛。可能是为了保持运河两岸“黄中透绿”的色彩特点,他大多采用漫射光拍摄,不让光照参与造型。这样的图像语言复与运河的功能相结合,便得到一组意趣和视觉完成度均属上乘的系列组照。贾江凡因故晚到了一天,但他行前研究了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作品。他从这些作品中提炼出显著的视觉要素,再返回丰子恺故乡的现实中进行搜寻和创作,同样合格地完成了拍摄任务。贾江凡的工作方式正是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哲学家、思想家)图式嬗变方式“p1-tt-ee-p2”(波普尔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通过不断提出尝试性猜想,并不断清除其中的错误而得以实现的。在他提出的“四段图式”中,“p1”表示各种问题,“tt”为各种理论,“ee”表示反驳清除错误,“p2”表示新的问题。——编者注)的体现——“p1”乃是他选定的初始图式,“tt”是他采用的技术手段,“ee”是通过去谬进行优化,“p2”则是最终得到的图像。
宋晓丹和王丝雨则展示了一个永恒主题:创伤。创伤与自我与生俱来,尤其在“女性”摄影师这里,创伤这个话题总是常说常新。王丝雨、宋晓丹都隐晦地展示了她们自童年延续至今的痛楚与困扰,所不同的是,王丝雨通过撷取现实的物象以“移情”的方式表现了她被束缚、被规训的痛苦,宋晓丹则用极具象征性的物品造景,以“通感”暗示了逝去的脆弱与无奈。王丝雨试图从现在回到过去,宋晓丹则由过去遥想未来,她们的坦诚令人动容,相信这两个女孩子或直面或粉饰的影像能引起共鸣,让观者与她们一起获得疗愈。
与宋晓丹一样,赵梦佳和何亚英杰都用闪光灯直率地参与了造型。强烈的直射光不再是对现实之物进行显像的技术要素,而是为隐喻的主体敞开了一个更深邃的空间,它把散漫的背景猛然推向黑暗,却把主体一丝不挂地摆上明亮的祭坛,刺目的平面感赤裸裸地展示了无可名状的惊惧,意义却不得不从空洞的暗处向更深更远处逃散。赵梦佳有意指向梦境的支离破碎,何亚英杰则从女友日渐消失的文身中看到了真实的无从把握。他们的照片都像随记性的俳句,在偶然的情景、微细的褶皱、虚空的裂隙和无所住相的刹那中无意识地驻足。这些微不足道的、稍纵即逝的搽痕是生命的碎屑和时间的余数,有质感有张力有回响却无从依附,所谓“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徒唤奈何?
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摄影的自我放飞越远,目光却落得越近。新闻报道摄影从来关注的是他者,是外在,是远方,而新型的摄影者则是重新发现附近,或干脆重新发现自己。但他们并没有试图建造一个以个人为中心、自言自语、自给自足的精神乌托邦,而是以“自我”作为方法,以具体可感的个人经历与经验为诚恳背书,重新丈量和定义生命价值和生存质量,让摄影不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组织起来的道德;不再宣泄个人情感和情绪,而是致力凝结情感概念和人类意志;不再以“善”为借口来说教,而是对“恶”进行不动声色的披露。他们尽可能地用自己的语言和材料,表达自己对当下的感受和认知。于是,那个曾经一度相当出格的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那句警言“重要的不是拍政治性的电影,重要的是政治性地拍电影”,就被借鉴为当代摄影的重要策略。赵凡瑜的《会》便用这样的策略,既交代了事实,又表达了感受,二者的化合物进一步充当了我们每个人经验的催化剂,其“内爆”的力量可想而知。
就在我写这篇小文时,第四届拾城摄影奖初评结束,4000多人参加的这个奖项有278幅照片进入终评。与工作坊学员的“作业”相比,那些秉持新闻专业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摄影师仿佛留在了我们曾经初心所向的那个世界,他们甚至更加极端地试图用单张照片把事实与象征捏合在一起。但如果艺术就是以向当下的世界发问为出发点的话,那么这些看似形态各异的摄影又有什么不同?所有坚持在现实中寻找和定格超现实瞬间的摄影者,在象征的世界里又何尝不是平行的同路者?尽管“诗与远方”被消费主义和流量经济牢牢绑定,充满诱惑,但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终究还在此处、在附近、在自己的世界里?
举报 收藏 点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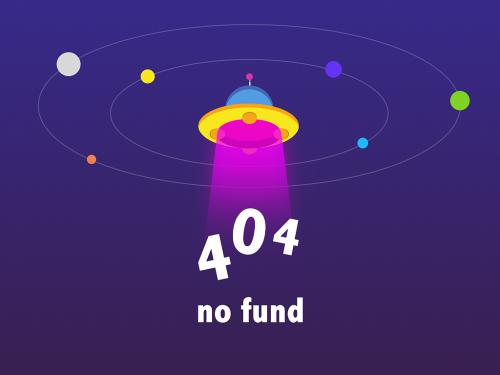

我要评论